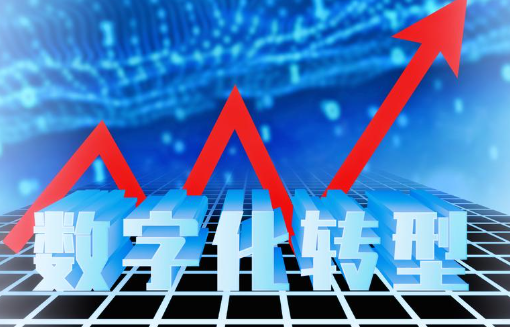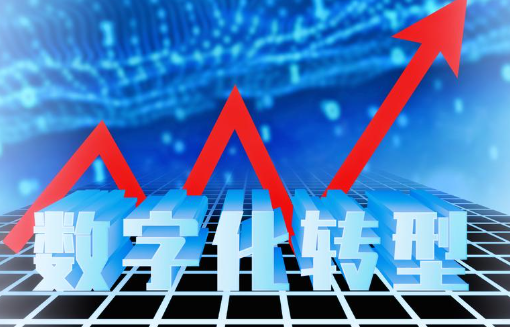“数字化转型”之难,究竟难在哪里?
发布时间:2023-05-18
浏览次数:320
来源:总裁读书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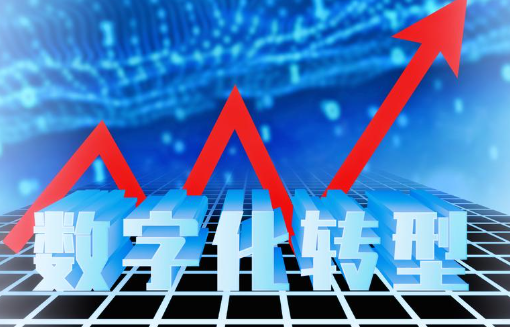
GE数字化转型失败引发的思考:数字化转型,究竟难在哪里
通用电气公司(GE公司),是美国的跨国综合企业,由伟大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创立于1892年,至今有130年历史,主营业务包括工业设备和家用电器。
2001年,杰夫·伊梅尔特从被誉为“全球第一CEO”的杰克·韦尔奇手中接过GE董事长的帅印,非常想做出一番新成就,而不是固守前任留下的江山。
2011年,杰夫·伊梅尔特推动GE走向数字化转型之路。
2012年,GE首次提出闻名遐迩的“工业互联网”概念。
2013年,GE推出工业互联网平台Predix,制订了雄心勃勃的数字化计划:服务GE自身,要实现卓越制造;服务GE客户,要提升客户成效;服务世界,要使Predix工业互联网平台成为工业操作系统,赋能全世界的工业企业。
2015年,GE数字化部门成立,GE也为这个部门制定了一个宏伟目标:五年内软件及相关服务销售额超过150亿美元,2020年跻身全球十大软件公司之一。从中不难看出,杰夫·伊梅尔特的战略变革方向:希望把GE定位为软件公司而非制造企业的决心。
然而,GE累计超过40亿美元的数字化投入,并没有带来股民期望的财务回报,上述目标基本没有得到实现,GE数字化部门的收入主要来源于GE内部的其他部门,商业模式并没有闭环。
2017年,GE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股价下跌,市值蒸发超过1000亿美元,主导GE数字化转型的董事长杰夫·伊梅尔特在年底被迫辞职。
2018年年底,GE正式剥离数字化业务,从致力工业互联网开放平台的建设,回到了聚焦自身制造业务上,长达八年的数字化转型之路宣告失败。
GE数字化转型失败并非孤案。2021年全球著名咨询公司埃森哲和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领军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成效达到预期的,只有16%。
这意味着,即便是那些要资金有资金、要人才有人才、要顾问有顾问、要技术有技术的领军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也依然困难重重,超过八成没有达成管理者的变革预期。这不得不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数字化转型,究竟难在哪里?
“数字化转型”之难,不在于“数字化”,而在于“转型”
关于这个问题,我先把自己的结论抛出来:“数字化转型”之难,不在于“数字化”,而在于“转型”——“数字化”解决的是生产工具的升级换代问题,“转型”解决的是生产关系重新达成共识的问题。这并不是说生产工具的升级换代不艰难,而是因为生产关系重新达成共识的难度,比生产工具升级换代的难度复杂得多。
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最重要的标志,是人类会使用生产工具。但具体到个人,绝大部分工具都不是我们自己制造的,而是使用别人/前人已经无数次使用过、验证过的工具。这就像我们并不需要重新制造汽车轮子、不需要重新研究汽车发动机,只需要会开车,就可以享受汽车带来的巨大便利——工具之美,在于应用。
人类的协作产生了生产关系。然而,有人的地方就有市场、有利益、有价值观,这个是动态的,比生产工具的“物”本身的静态性复杂得多。
正因如此,如果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时能梳理清楚生产关系,则生产工具可以由大量的专业人士提供,供企业选择。毕竟,在应用这些生产工具之前,已经有无数的企业使用工具并留下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已足够企业驾驭工具这个静态“物”。
2021年,华为首席信息官在公开演讲时有过一个论断:任何不涉及流程重构的数字化转型,都是在装样子。这句话很快被媒体注意到并解读。它的意思为数字化转型一定不是以生产工具为核心的,而是以生产关系的调整为核心的——流程重构的背后是利益格局的重构。
就像“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把自己定位为社会旁观者,因为管理的基础是人和社会,人是指自然人,是具有个体人性状态下的“人”,讲究“人性”;社会是指人在群体中的生存状态,讲究“社会性”,谈论“管理”而不谈“社会”就是纸上谈兵。
数字化转型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变革工程,推动这项变革犹如移动一座冰山。大多数人只看到冰山在蓝天、白云映射下的美,却没有看到冰山下的凶险,因此没有敬畏之心。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是显而易见的数字技术变革,但这是生产工具;冰山藏在水面之下的部分则是企业内部、上下游伙伴的生产协作、利益交易,这才是生产关系。为了移动整座冰山,企业必须付出足够耐心调整水面下的那一部分,否则冰山很容易分崩离析。
大多数企业数字化转型之所以失败,最常找的托词是数字技术和企业自身的业务不匹配,其实不是因为技术与业务不匹配,也不是技术专家不懂业务,而是转型改变了水面下的利益格局引发反弹。
变革主导者往往高估了转型后的美好愿景,而低估了那些被动了奶酪的人所形成的巨大阻力。利益既得者不支持变革,新的权责利分配机制没有达成共识,进而以技术专家不懂业务为由拒绝变革。公司规模越大,公司成立时间越长,路径依赖现象就越明显,利益格局的板结状态就越严重,数字化转型的推动难度就越大。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场变革中得到经验和教训。
这四场著名变革有一个共同点:拥有一个热烈拥抱变革的幕后老板,以及一个深得老板信任、身兼总架构师及项目经理的变革者。
距今2300多年前,一场著名的变法正在秦国展开,如果视变法为一个行为项目,则项目经理是商鞅,其幕后老板是秦孝公,史称“商鞅变法”。
距今950多年前,又一场著名的变法在北宋拉开序幕,项目经理是政治家兼文学家王安石,幕后老板、皇帝宋神宗给予这场变革大力支持,史称“王安石变法”。
距今450多年前,明朝中晚期,首辅张居正亲自担任项目经理,在幕后老板、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大力支持下掀起一场改革,史称“张居正改革”。
距今120多年前,晚清末年,年轻的光绪皇帝试图力挽狂澜,启用康有为担任项目经理,史称“戊戌变法”。
当我们复盘这四场变革,不难得出一个共性结论:中国历史上任何一场变革,都因为改进生产工具、提升生产效率而得到民众的拥护,却也都因为改变生产关系、重塑利益格局不当而被利益既得者强烈抵触乃至扼杀。
华为是一家把变革常态化的公司,任正非很注重以史为鉴,曾经对此做过评述:
“我们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变法,虽然对中国社会进步产生了不灭的影响,但大多没有达到变革者的理想。我认为,面对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他们的变革太激进、太僵化,冲破阻力的方法太苛刻。如果他们用较长时间来实践,而不是太急迫、太全面,收效也许会更好一些。其实就是缺少灰度。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并不是一条直线,也许是不断左右摇摆的曲线,在某些时段来说,还会画一个圈,但是我们离得远些或粗一些来看,它的方向仍是紧紧地指着前方。”
以上四场变革的项目经理,结局都不好。商鞅被五马分尸,王安石在变法失败后郁郁而终,张居正被抄家,康有为被迫逃亡。可以说以上四位项目经理在各自的时代开展变革时,最具备“人和”条件的是张居正——幕后老板万历皇帝是他的学生,对他提出的举措言听计从(万历皇帝10岁即位,张居正是其老师,被称为“万历首辅”),但他最终未能善终。
华为的每一场变革,包括信息化改造、数字化转型,都遵从“之”字形变革法,聚焦共同目标,顺着如下路径演进:老板知→全员知→试点行→全员行。
中国很多企业变革的失败教训:从“老板知”到“全员行”,中间没有切换轨道,也就是在“之”字形变革法A模型中直接从“老板知”跨到“全员行”,把“全员知”“试点行”都省略了,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失败概率极高,最后连变革主导者自身都沦为变革的牺牲品,让人扼腕叹息。
在华为成长史上,遵从“之”字形变革法最典型的案例是《华为公司基本法》的起草。这个文件全文一共才1.6万字,1996年3月开始起草,1998年3月正式颁布,历经三个年头,八易其稿,动员公司上下几千人展开多轮讨论,深入人心。任正非评价:“《华为公司基本法》颁布的那一天,也许是它完成历史使命之时,因为它已溶入华为人的血脉。”
从文件起草本身的难度来看,用不了这么久,但这是开展“全员知”的松土过程,是在对新的生产关系达成共识的过程,急不来。经过《华为公司基本法》松土之后,华为1998年开始把IBM引入,掀起了浩浩荡荡的企业变革之路,包括IT S&P(IT战略与规划)、IPD(集成产品开发)、ISC(集成供应链服务)、财务“四统一”、LTC(从线索到回款)、IFS(集成财经服务)等。
2008年2月29日,华为举行了IBM优秀顾问的答谢宴会,感谢1998年以来帮助华为变革的IBM顾问们。IBM公司1998-2003年派驻华为负责华为与IBM咨询项目的总项目经理陈青茹在答谢宴会上讲了如下一席话:
“IPD流程本身不是最有价值的,它的管理理念才最有价值。华为的各级管理者如何管理IPD,他们的理念如何,是要大家去体会和学习的,如果人不改变,流程就是没有用的,就不能深刻理解任总讲话的真实含义。所以要先看自己是否愿意改变?如果不改,顾问也帮不上什么。”
我们不难想象:IBM顾问进场之前,如果华为自身没有1996-1998年历经三年《华为公司基本法》自上而下的松土工作,IBM带来的那一套西方管理体系想在华为落地将是何等艰难之事。
数字化转型的难易程度,取决于管理者对数字化转型是否达成共识
复盘多个企业数字化转型失败案例后,我们可以发现:数字化转型的难易程度,并非取决于企业规模的大小,而是取决于这家企业的管理者对数字化转型有没有达成共识。也就是说,800人规模的企业,并非比8000人规模的企业更容易转型成功。
正如《庄子》语:“井蛙不可语海,夏虫不可语冰。”如果公司内部对数字化的理解和认知水平参差不齐,那么即使只是800人规模,开展数字化转型也是寸步难移。
根据华为的经验和业界的实践,共识主要包含三个要点。
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顺应市场和客户的需求,利用新一代数字技术开展的业务转型和管理变革工程,并非技术转型,因此需要业务部门管理者的全身心参与,将其视为自己部门的事情,而非委托给IT部门或外部咨询顾问。
“行动三问”包括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一切转型都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而不是成为别人。因此数字化转型要以“我”为主,通过管理者的多轮反复讨论,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开展。
美的集团自2012年启动数字化转型以来,至今已有10余年,累计投入超过170亿元,如今它依然不遗余力地推进数字化转型,而且随着进入深水区,待解决问题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2021年2月,美的集团董事长方洪波接受学者杨国安专访,谈到他作为一把手推动数字化转型的焦虑:
复盘美的整个转型过程,最焦虑的决策,是数字化转型的投入,例如当年搞632投入20亿,包括之后每年都要投几十亿,每到这种需要做出抉择的时候都会感到很迷茫。
在2017年之前,无论是建设工厂、研发中心还是信息系统,我知道进行投资肯定没错,因为那是看得见的痛点,有明显需要解决的问题,能够非常清楚这些项目一定有回报。
但到了2017年,面对数字化这个隐形的东西,无法以肉眼去判断、以经验去判断,甚至有时候不知道方向在哪里,我想这是目前最大的困难。我有时候心里也在问,到底往前走会怎么样?它也是未知,这就是最大的焦虑。
目前,我想我所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推动、决策,不断往前推。简单来讲,数字化的推动一定是一把手工程,如果一把手不推,永远推不动。如果一把手想推,再大的困难也会解决。有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靠一口气,这一口气突破了、顶住了,可能就是一片新的天地;但如果有时候没有憋过去,又会回到起点。
无独有偶,距离美的集团顺德总部120千米的华为深圳坂田基地,也上演着同样的故事。
华为自1998年启动ITS&P变革至今已经25年了,即便除去流程驱动的时间不算,从2007年孟晚舟基于数据驱动的理念对财务体系进行数字化转型算起,至今也有16年。华为每年按销售收入的1.5%~2%划拨资金投入数字化转型,至今依然看不到画上句号的那一天。
或许数字化转型这条路永远没有句号——这不是一个有限的游戏,而是一个无限的游戏。
就像跑马拉松一样,中间有一段感觉很艰难,如果能挺过去,那么迎接我们的将是胜利。经历变革后的华为,取得了巨大成就,享受到变革带来的红利。
关于上述话题所讨论的关键,复旦大学经济学家兰小欢所著的《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与经济发展》一书中也有相关阐述:
“公众所接触的信息和看到的现象,大都已经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博弈后的结果,而缺少社会阅历的人容易把博弈结果错当成博弈过程。即使在今天,中央重大政策出台的背后,也要经过多轮的征求意见、协商、修改,否则很难落地。成功的政策背后是成功的协商和妥协,而不是机械的命令与执行,所以理解利益冲突,理解协调和解决机制,是理解政策的基础。”
从中国历史上的四场著名变革,以及华为1998年以来的一系列管理变革,得到什么启发?以下是我在“管理的数字化转型”课堂上的一段总结语,期待能给你带来新思考:
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如何应用现代数字技术升级生产工具不是核心挑战;如何顺应时代、市场、客户、供应商、经销商、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的诉求,改变生产关系才是真正的核心挑战,数字化转型最耗费时间的环节是对新生产关系达成共识。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最先探讨的问题其实是利益格局有可能怎么动。